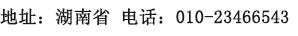我不是个乐观主义者,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,内心对前途的不确定总是充满了莫名的焦虑和不安,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,脑子就像个嘈杂的剧场,很多不存在的场景都会出现,有时候会让自己的天灵盖疼,只能用三九正天丸来解决问题。
时间长了,我担心自己会变成日本电影《追捕》里的横路靖二,从高楼上一直朝前走,最后融化在蓝天里。
悲观主义者的下场都不好,要不像诗人那样卧轨了,要不像梵高那样把自己的耳朵割掉了,自己身上的器官又不是韭菜,怎么能随随便便割掉呢,割掉了又不会长出新的来。
我不喜欢悲观,悲观者基本上属于情绪动物,身上的情绪就像趵突泉的泉水随时随地往外涌,动不动就菊花残,满地伤,你的笑容已泛*,花落人断肠,我心事静静淌。
这种情绪对自己倒也罢了,但问题是它能影响别人,就像民间评论一个郁闷的人:“你看他那张丧脸,就好像谁都欠了他块钱一样。”
为了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被人憎恶的人,我比较喜欢选择带乐观色彩的读物,好让自己乐观起来。
努力了很久,发现基本上没能实现自我改造,只能保证自己不会去卧轨,也不会割掉自己的耳朵,总体上还是一个悲观的人。
但我身边却不乏乐观的朋友。
我的朋友陈斌是个职业司机,专门为酒店接送去机场的客人。
胖人多乐观,陈斌就是个胖子,长了一排整齐的大白牙,他爱笑,一笑,那一排白牙就像大阅兵的士兵,我怀疑他爱笑是不是为了显示他的白牙,是一种炫耀。
好像没见过陈斌不开心的样子,他什么时候都是一副对生活充满了幸福感的样子。
有次我有事去找他,他说要先去拉个客人然后才能有时间,在等客人的时候,望着深秋的一派萧瑟,我一点也打不起精神。
陈斌饶有兴致的看着车窗外的景致,突然他拍拍我:“你看这些落叶,要是漫天飞的都是钱多好,我们快下去捡吧。”
树上五彩斑斓的树叶被风一吹,纷纷扬扬的往下飘,这本来是秋日里的常景,但被陈斌这夸张的形容,我也高兴了起来:“就是啊,这要是漫天飞的都是钱,咱们可就发大财了。”
陈斌说:“我把后备箱所有的东西都扔掉,腾出空间全装钱,把车装满,然后开车去你家数钱,然后平分。”
接下来,我们就认真的讨论有了这么多钱要干什么呢,买个大房子,买辆好车,先去旅游,徜徉在祖国的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中,然后开个餐厅,装修的别具特色,打造成网红餐厅,美丽人生从此开启。
我们就像两个傻子,就在这虚拟的场景里自我陶醉。
这一天之后的时光都是轻松的。
不得不说,乐观的人看这个世界的眼光真的不一样,平平淡淡的东西都能让他演绎的有声有色。
我认识了一个快乐的姑娘,她是一个导游,叫素素,因为参加了一个单位考察学习团,认识了这个导游,除了一路上她把我们所有的行程安排的妥妥帖帖以外,她用自己的快乐感染了我们所有人,让大家很开心轻松。
考察学习行将结束时,我问素素:“你有不开心的时候吗?”
素素眨眨眼:“有啊,可我一有不开心的时候就会给闺蜜打电话,约她们出来吃饭,喝酒,K歌,好一通嗨皮,闹累了回家倒头就睡,第二天想半天想不过来,就给闺蜜打电话,我们昨天为什么要喝酒?人家说,是你说自己不开心组的局啊。那我当时是因为什么事不开心的呢,怎么想也想不回来,这不烦恼没了,多好玩,哈哈哈。”
素素的乐观真不是装的,第二天我们要离开酒店乘车时,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我们的大巴旁,有人说这是素素的爸爸,来看女儿。素素远远的开始一路狂奔,然后嗖的一下飞骑到老爸的背上。
这一刻,她一点不像本应该矜持的姑娘,而像个挂在父亲身上的考拉,很可爱,很温馨。
我现在想明白了,乐观是浑然天成的,是上天给一个人特别眷顾送的礼物,是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温暖同伴,愉悦自己的别致气质。
上天如果没有赋予我们这样的气质属性,也无所谓了,至少我们知道乐观是个好东西,那就多接触乐观的人。让他们的快乐来感染自己,反正这世界末日你是亲眼看不到的,何必让自己活得那么沉重纠结和惆怅呢。
不开心了,想想漫天飘的全是钱,那就开心了。
文/赵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