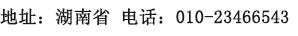考拉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野生动物。然而,据预测它们将在未来30年内灭绝。有科学家认为,了解考拉与人类的关系可能有助于拯救这个物种。他们的研究通过追踪考拉在自然历史书籍、儿童故事、明信片和旅游小册子中的表现来检验这种动态。
这项研究帮助人们对考拉的态度从科学和经济观点转变为更浪漫、更感性的态度。特别是,考拉与人类婴儿有着共同的身体特征,这使它们更受我们的喜爱。拟人化可以触发人类积极的情绪,这有助于保护行动的开展。然而,对考拉的威胁归根结底是某些决策带来的结果,而情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。
当人类在其他动物身上看到自己时,会产生更大的同情和关心。而考拉,以其人类婴儿般的形象可以很容易地产生拟人化的效应。事实上,考拉表现出的“新生”,即成熟的动物保留幼年的身体特征,这已经被证明能激发成人积极的情绪反应。
当人们看到婴儿时,通常会很愉悦,而且心中会充满怜爱之情和保护欲,这是我们人类千万年来进化的结果。从深层次来说,婴儿的体态或表情会激发我们大脑的“奖励机制”,会产生多巴胺。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,可以帮助细胞传递脉冲物质,当我们看到婴儿的萌态时,多巴胺就会开始发出信号,刺激我们的大脑,让我们产生幸福感和快乐感。这套机制使得成年人自发地去保护婴儿,最终使得人类种族得以繁衍。
这套机制在考拉身上也同样适用。考拉跟人类婴儿有不少的相似之处,包括:突出的前额,位于头部中心以下的眼睛,圆头圆体,体表柔软而富有弹性……
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出版的报纸文章经常把考拉的形象刻画得更“萌化”。例如,《格伦·因内斯考官》的一篇文章将考拉称为“小熊”,它们“像婴儿一样坐在树上”。实际上,考拉在受伤或心烦意乱时也会发出哭声,这一点使得它们更像婴儿。
但考拉并不总是受到后殖民时代澳大利亚人的喜爱。最早的记载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,有称它为猴子、树懒、狐猴和熊的。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,澳大利亚人主要通过独立的科学视角来观察考拉
同时,考拉也被视为一种经济资源。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,成百上千的考拉被猎杀,最终成为毛皮贸易的牺牲品。
进入20世纪,考拉的动物学表现继续在自然史上出现。其中包括年出版的《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》,该书指出:“考拉,或称本地熊,一种可能比任何其他野生动物更能吸引澳大利亚人的动物,其天真、幼稚的表情以及安静、无害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吸引人们的喜爱。”这段文字表明了一种更浪漫的观点,认为考拉与人类相似,考拉才开始在人们心中变得“可爱”。
年出版的两本书鼓励公众喜爱考拉。诺曼·林赛(NormanLindsay)的《魔法布丁》中有一个被拟人化的考拉角色,名叫BunyipBluegum,穿着漂亮的休闲裤、夹克和领结。这些书的读者比自然史要多得多。当年昆士兰州宣布捕猎考拉的开放季节时,很多人开始对这种活动表现出愤怒,并表示抗议。
摄影在20世纪的迅速崛起也巩固了考拉的公众吸引力。成群的考拉被安排将照片复制成明信片,通常标题是“澳大利亚的泰迪熊”。动物学家埃利斯·特劳顿(EllisTroughton)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出版的《澳大利亚的毛皮动物》一书中记录了考拉在国民心理中的特殊地位:“这只迷人而无助的孤儿在漫画和故事中已经闻名于世,它比他们领养国的任何其他动物都更能博得澳大利亚人的喜爱。”
考拉的流行催生了一个新兴的旅游业,它渴望在全球旅游市场上创造民族特色。如今,考拉的形象仍被印在茶巾、t恤、明信片和其他纪念品上。考维德之前,考拉对澳大利亚旅游业的经济价值估计高达每年32亿澳元。
考拉吸引的保护资金也远远超过大多数物种。例如,去年的研究表明,对考拉的保护资金远远超过了对北方毛鼻袋熊的资金。袋熊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,而考拉在澳大利亚部分地区被列为脆弱物种。
拟人化可以是一个强大的方式来产生